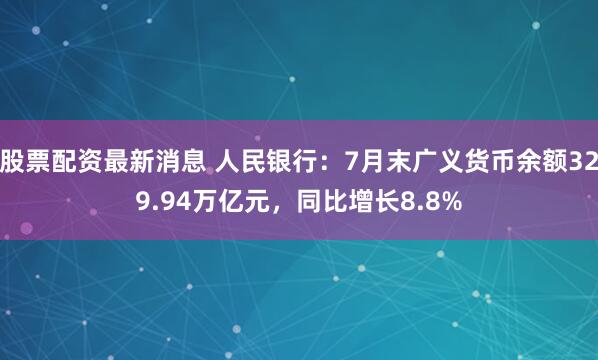独立评论人 邓启金 撰稿实盘配资排行榜
7月27日,在同志涉及刑事犯罪被多部门调查官宣后,笔者迅速写了一篇名为《释永信被查背后的权力、资本与信仰困局》的文章,剑指现象背后的实相,文章存活不到十小时就涅槃,不知道是不是文字触及到了真相背后的大树,于是重新撰文,用释永信的图片遇上土家铁拳的文字,来勾勒这末法时代的妖魔鬼怪和魑魅魍魉。
2025年的盛夏,山门外的电子屏滚动着“第十一届少林文化节”的广告,香客们举着手机在武僧表演区前打卡,禅房里飘出的不是梵呗,而是旅游团的扩音器声。这座曾被禅宗六祖惠能称为“佛法正宗”的祖庭,在当代中国的舆论场中,正以一种割裂的姿态存在——一边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的“文化名片”,一边是被戏称为“少林集团董事长”的释永信和他治下的商业帝国;一边是信众心中“普度众生”的修行者,一边是被舆论标签化的“政治和尚”。

这种割裂,恰是末法时代佛教乃至其它宗教在中土处境的缩影。
佛教经典中的“末法时代”,原指佛陀涅槃后教法逐渐衰微的时期,其特征是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”,修行者难持戒律,信众易惑于表象。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,这种“末法”已不仅是宗教内部的信仰危机,更演变为整个社会文化生态对宗教的功能性阉割——当传统信仰体系遭遇科学理性、消费主义与世俗权力的三重冲击,宗教要么退守为少数人的精神私域,要么主动(或被动)融入世俗社会的运行逻辑,成为权力或资本的“功能性工具”。权力要宗教软化百姓脊梁骨,壮实膝盖骨,阉割反骨和傲骨;而资本需要袈裟作为道具,把信众变成韭菜,信仰变为流量,把彼岸变成当下的变现。
少林寺的选择,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困境的极端样本。作为汉传佛教禅宗的祖庭,它本应承担着“续佛慧命”的宗教使命,但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政策、旅游经济与地方发展需求的多重压力下,其宗教属性被不断稀释:1982年《少林寺》电影的火爆让这座古刹进入大众视野,1990年代“少林寺海外建分院”的商业尝试开启国际化之路,2000年后“申遗”成功将其推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,而近年来“少林IP”的全面开发(从动漫到电竞,从武术培训到健康产业),更使其成为横跨文化、旅游、教育、商业的综合性集团。

这种转型看似“与时俱进”,却也埋下了深刻的矛盾:当少林寺的门票收入(2015年曾因涨价引发争议)、商标授权费(“少林”商标注册超700项)、武术表演收入成为主要经济来源时,“禅修”与“商业”的边界逐渐模糊;当方丈释永信频繁出席政府会议、参与社会活动(甚至被媒体曝光与地方官员的密切互动)时,“高僧”的形象与“文化使者”“经济推手”的角色重叠交织。公众的质疑也随之而来:这座千年古刹究竟是在“普度众生”,还是在“经营众生”?少林寺作为载体和道具,释永信作为主演和手套,背后的制片和导演又是谁?
“政治和尚”的标签,本质上是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简化想象。在中国,宗教团体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活动,接受政府的管理,这是基本国情,也是实情。少林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,其文物保护、文物保护资金使用、僧人管理等事务,本就属于政府监管范围。释永信作为少林寺住持,参与地方文化事务、推动旅游发展,某种程度上也是履行宗教团体服务社会的职能。但舆论场中的“政治和尚”叙事,直接指向的是政教互动的“攀附权贵”和“权力寻租”。

这种叙事的背后,是公众对“宗教纯洁性”的焦虑。在一个信仰多元的社会里,人们可以接受寺庙卖门票、僧人用手机,却难以容忍宗教场所成为权力的“附属品”。当释永信被卷入多起法律纠纷(如2015年的“私生女”传闻、2020年的“挪用资金”争议),尽管多数指控最终未被司法认定,但这些舆论风暴却在不断强化“宗教被权力污染”的集体认知。
而“少林董事长”的标签,则指向宗教商业化的伦理困境。少林寺的商业布局确实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:据统计,2024年少林寺景区全年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,周边文化产业收入突破30亿元,这些资金被用于文物保护(如塔林修缮)、慈善事业(如“少林慈幼院”收养孤儿)和宗教活动(如水陆法会)。但商业逻辑的渗透,也在悄然改变少林寺的生态:武僧团从“修行者”变成“表演者”,禅修营从“修心”变成“研学”,连寺内的香火售卖都引入了“会员制”。当宗教仪式被包装成文化产品,当修行场所变成打卡景点,人们不禁要问:少林寺的“禅”,究竟是让人“明心见性”的佛法,还是刺激消费的营销手段?
需要思考和诘问的太多,笔者想说的是:文字和图片背后的“少林派”斩首行动,只是对少林派的定点清除,还是各大门派的灭门之灾?














七星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